“最后,我觉得自己被理解了,我并不孤单,这不仅仅是我的幻觉

评论:两年前的今天,我数着自己的幸运星。
深夜在法国里昂参加大学交流活动时,我喝醉了,没有戴头盔,骑着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了。
不知何故,我逃了出来——当时我认为——相对毫发无损。我在医院住了一夜,但由于“轻微的头部受伤”和脚踝扭伤,第二天下午我就被送上路了。老实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感觉还好。我头很痛,一瘸一拐,但除此之外,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我已经准备好摆脱它,继续享受我的海外冒险。
我想小心一点,不要夸大其词,虽然真的没有必要。我经历过慢性头痛、使人衰弱的焦虑和摧毁灵魂的抑郁。有几次,我真的找不到出路,从无尽的绝望中走出来,我觉得自己被困在那里,我深深地思考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花了很长时间,但我已经找到了我需要的治疗方法,以便恢复正常的生活,最后,我觉得隧道尽头有一束光。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写这篇文章,这样其他头部创伤的受害者就不会像我一样遭受痛苦。这样他们就可以寻求迅速和适当的治疗。
正如我所经历的那样,有效的脑震荡和脑震荡后综合症多学科诊所少之又少,但我乐观地认为,随着围绕这个问题的对话越来越多,这个国家的医疗专业人员和有效治疗设施的数量也在增加。
在我受伤的时候,我从未听说过脑震荡后综合症或持续的脑震荡后症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残酷而激烈的折磨会如此持续不断。但当我感觉自己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迅速完全康复时,我相信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
朋友和家人从家里联系我,表达了他们的震惊和担忧,我对大多数人的回复是:“我很好。实际上很好。只是几处割伤和擦伤。会完全康复的。”我妈妈直接飞过来陪我。她是在事故发生四天后到达的。“真的,我很好,妈妈。你不应该这么麻烦的”,我告诉她。
最令我恼火的是,我不得不重新安排大学考试的时间。我错过了学期结束的庆祝活动——我所在大学的大多数交换生都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去法国学习是我的梦想,我正享受着生活中的美好时光,但它突然被打断了。“真烦人,因为我现在应该去度假了。哦。还可能更糟呢。”
回想起这种心态,我非常羡慕。关心这些琐碎的事情是多么令人高兴和荣幸啊。
一个月后,我完成了大学的期末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这再次表明,我真的很好。我拿到了学士学位,开始认为这次事故不过是一次小事故,尽管带来了非常恼人的不便。
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当我喝着早晨的咖啡时,我的胳膊和腿颤抖着,我的血管跳动着,我的头砰砰作响。阳光耀眼地照进我的眼睛,附近的声音像扩音器一样回荡,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我感到幽闭恐惧症,头晕目眩。
结交新朋友、体验新文化的强烈愿望开始消退。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结交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和他们一起,我经历了如此强烈的幸福,并使自己成为了能量和积极的源泉,我懒得和他们一起庆祝告别。
我并不想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但在朋友们的要求下,我参加了。
在一家破旧的巴黎夜总会里,我被墙围住了。砰砰的音乐使我的耳朵颤抖,我的头感觉要爆炸了。这是第一次,这些新的和不和谐的感觉控制了我,我向门飞奔而去。
我现在知道出了什么事。
所以,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绝大多数搜索结果返回的是:脑震荡症状:头痛、抑郁、情绪波动、焦虑。通常持续8天到6周。好好休息,恢复健康。”
“呸!”我想。真是如释重负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很正常。
“这才一个月,所以接下来的几周我会放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计划在完成学业后无限期地在欧洲工作和旅行。一个月后,我家里的朋友们就要来了,他们将踏上年轻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留下来,并在尼斯订了一家旅馆,住几个星期,以保持低调。
尽管有无尽的阳光和蓝绿色地中海的咸味,但我一点也不快乐。但我的身体症状有所减轻——我每天都会感到头部前部隐隐疼痛,但最初对光和声音的敏感性无疑有所减弱。
我以为我在好转。“等我的朋友们来了,我会感觉更好的。”我对自己说。
果然,当我在伦敦和女朋友团聚时,我感觉好多了。事故发生两个半月后,在我的脑海里,我回来了。然而,那天晚上我喝了两杯啤酒,睡得很糟糕,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头痛得厉害,你可以把它卖给科学界。我说这话是开玩笑的,但当时我很担心。我的精力耗尽了。
事后诸葛亮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回想起来,我绝对应该回家,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那就早得多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知道有脑震荡后综合症这种东西。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脑震荡。医院称其为“轻度头部损伤”。当时我和医生之间没有对话。我记得我对我的室友说:“我是不是脑震荡了?什么是脑震荡?”她回答说:“我想是的,因为你被打晕了。”
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但最终,我更担心的是可能有更险恶的事情在起作用。
“也许我脑出血了”,“也许我的大脑肿了”,我想。里昂的医院给我做了CT扫描,没有任何明显的生理问题,但这些想法还是开始占据上风。
我不忍心告诉我的女朋友和朋友们我只想回家。为了他们,我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当他们问起这次事故时,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我很好。”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傻,但很难表达出这种感觉。在这一点上,我的症状在身体上并没有过度衰弱。不像因为断腿而打石膏,我看起来完全好极了。有些日子我觉得自己有80%是自己,大多数日子只有一半是自己,有些日子我就像个空壳。
我的头痛从轻微到剧烈,恐慌和悲伤转瞬即逝。然而,这足以在我的脑海里播下怀疑的种子:“也许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许是流血”。
回想起来,我不想面对现实,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太好。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让周围的人看到。当时正值欧洲的盛夏,我正在度假,周围都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正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经常有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
我回想着自己的笔记:“自从那次事故以来,我一直感觉不像自己。我在里昂度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四个月,但这让我在那里的时光变得糟糕,从那以后,我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我有时感觉很好,有时又不太好。大多数情况下,我试图忽略持续的头痛和情绪波动。天啊,太累了。再加上旅行,工作太累了。自5月份以来,我一直带着行李箱生活:每周最多三次登上火车、飞机和公共汽车。旅行应该是有趣的。我觉得自己抱怨得像个孩子,但我只想回家。”
在我女朋友生日的那天早上,我和六个朋友住在爱彼迎(Airbnb)上,我无法从床上爬起来,这让我再也无法掩饰。我们前一天庆祝过了,我顶着头痛和严重的疲劳度过了庆祝。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考虑着叫救护车,因为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我确信它会从我的胸膛里跳出来。我脑袋里的神经剧烈地跳动着,我确信它们会破裂。当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世界在我周围旋转,当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就像被棒球棒击中了两眼之间。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蜷缩在爱彼迎的床上。整整五天,我都没有离开卧室,被严重的恶心、头痛和发冷所困扰。孤立和恐惧,我去互联网上寻找更多的答案,但我的搜索没有让我发现一个显著的少数-大约30% -头部受伤的患者继续经历持续的脑震荡后症状。
最后,在受伤四个月后,我放弃了旅行计划,订了一张回墨尔本的机票。尽管我很担心,但我还是乐观地认为适当的休息和恢复以及与医生的预约会对我有所帮助。我告诉我的朋友,当他们几个月后旅行结束时,我就会恢复正常。
长途飞行和随之而来的时差使我的症状严重恶化。我好几天都睡不着,经常感到恶心,有时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
我预约了我的全科医生,在那里我被推荐去做脑部扫描,并去看了一位专门研究头部创伤的神经科医生。最早的预约是在三个月之后。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头痛减轻了,身体也平静了下来,当CT扫描显示我没有任何损伤时,我真的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把自己沉浸在我喜欢的活动中——我离开时错过的东西。然而,一切都不像它应该的那样。冲浪让我头晕,跑步让我头痛,举重让我头晕。我当时是一名家具搬运工,只要拿起一把椅子,或者在卡车上翻过一个减速带,我的头就会悸动。
经过几天的工作后,我完全筋疲力尽,而在过去,我喜欢这份工作的长时间工作和对体力的要求。有几个清晨,我不得不打电话给老板,向他道歉,说我那天生病了,不能上班了。那些夜晚,我一直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的大脑在震动,我的身体在抽搐,我没有合眼。我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担心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的精神状况逐渐恶化。我感到很沮丧。偶尔会有困惑和恐惧的时刻,我的焦虑和担心使我瘫痪。我很累,但总是紧张不安。
过去,我在桑拿浴中找到了放松,但现在把自己暴露在高温下,让我的身体感觉好像要停止工作了。我呼吸急促,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在这里经历了第一次焦虑发作。我非常慌乱、恐慌、困惑、瘫痪:“我怎么了?”我想。
我尽力维持自己的社交生活,但在朋友21岁生日派对上,在一个拥挤的酒吧里,一切都变得太困难了。我只喝了一口啤酒就头晕目眩,砰砰作响的音乐使我的耳朵裂裂发抖。我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回到家时,我泪如泉涌。
我完全崩溃了,绝望了。我是聚会的中心人物,现在我几乎不能离开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光是熬过这一天就很艰难。
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女朋友都在海外。我看着我在墨尔本的朋友们都找到了全职工作,参加体育运动,参加派对。与此同时,我一天都无法不被恐慌占据,也无法去跑步、去健身房或在酒吧喝杯咖啡或啤酒。即使是最简单的任务也会让我不知所措。我感到孤独、无用、害怕和虚弱。
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而离我与神经科医生的预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于是我预约了一位与AFL有联系的理疗师。他们问我这样的问题:“今天是星期几?”、“一年中的几个月是往后的几个月?”还有用眼睛盯着笔看。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除了说我没有剧烈脑震荡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理疗师认为可能是我的脖子导致了头痛,并给我的全科医生写了一封信,建议我进行心理治疗。
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去找我的全科医生做心理健康护理计划,并转介去看心理学家。在六个疗程中,我留下的问题比答案还多。我感到更加疏远了。
我等不及要去看神经科医生了。为了治疗我的头痛,我去了一家骨科诊所,那里有一个“量身定制的脑震荡后治疗方案”,说实话,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整骨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眼睛和平衡测试,并据此断言我的症状是鞭打和创伤后焦虑的结果。听到脑震荡的消息,我松了一口气,我是“绿灯”。
整骨医生治疗了我的脖子,我重新开始工作,跑步,冲浪,打网球和健身房。我的头痛消失了,我感到很强壮,我的精力又回来了,虽然很短暂。
尽管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我还是很想睡,因为在10分钟的评估中,我用一条腿保持平衡,眼睛盯着一根棍子,向后回忆单词,这样就能得出明确的医学诊断。我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造成我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焦虑。
那次脑震荡已经过去七个月了,但我经常因为身体痉挛而在半夜醒来,我经常感到沮丧、疲倦、头晕,而且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沉思。我尝试了心理学、冥想、呼吸技巧、频繁的体育锻炼,但都无济于事。我非常希望两周后与脑震荡诊所的神经科医生的会面能给我一些答案。
然而,当时间到来时,我震惊地意识到,我已经等了三个月,才得到和以前完全一样的评估。“眼睛跟着笔走”,“单腿站立,闭上眼睛30秒”,“在走直线的时候倒着回忆一年中的几个月”,“给你的头痛打六个分”。
不到60分钟的评估令人失望。“我不担心你的脑震荡,”他们告诉我,“我担心的是创伤后焦虑。为什么不试试抗抑郁药呢?”
他们把我送走了,给我安排了三个月的检查。我得到的唯一建议是“不要喝酒”。那次约会结束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医生给我开了药,我服用了最低剂量的四分之一。
几个小时后,我就感到了严重的副作用:癫痫发作、出冷汗、恶心、头晕、头痛。
我咨询了我的全科医生,我们一起决定换药。
我心烦意乱,无助,绝望。没有出路。我确信我会永远这样。
我明白了事情总是会变得更糟。
我变得太害怕了,不敢独处,不敢社交,太累了,不敢走在街上。没有什么能分散我的恐慌。无论我是在看书还是看电视,它的爪子都深深地插在我的心里。
我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投射的光线突然变得太锐利、太亮了,我的眼睛甚至瞥了它们一眼就嗡嗡作响。我听音乐的时候耳朵会颤抖,稍微运动一下就会让我的头嗡嗡作响。曾经带来快乐的一切现在都带来了痛苦。我把它归因于焦虑。
当我出来见朋友时,许多人问我:“你的啤酒呢?”“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微笑着告诉他们:“我脑震荡了。”我从来没有诚实地说过我有多么痛苦,尽管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任何建议都只会让我更加偏执:“不要再踢足球了,否则你会得慢性阻塞性肺病”,“不要运动,不要看屏幕,不要出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我被我的脑震荡定义了。
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脑震荡成为了AFL和媒体的一个主要问题。著名的前足球运动员丹尼·弗劳利(Danny rawley)和谢恩·塔克(Shane Tuck)都自杀身亡,这是我的话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可以结束我的生命,”我想。“不管怎样,我最终可能会因此而死去。”这些想法让我不寒而栗,虽然我从来没有接近过采取行动,但我感到无能为力,就像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叙述一样——这是最让我害怕的。
在我看来,没有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为了解决我的无目的心理,我申请了悉尼大学的法律研究生。由于我的脑震荡已经从医学上清除了,我看不出全日制学习有什么问题。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城市里获得一个享有盛誉的学位:我认为它是万灵药。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该课程将于2023年2月开课。我激动得都等不及了。
在我出发前两周,暑假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的症状已经减轻了。我的头痛是存在的,但很轻微,只有在看屏幕时才有点不安。我在冲浪和跑步,虽然我很容易累,感觉很慢,但我把它归结为我在过去9个月里经历的焦虑。
我知道了压力对脑震荡的影响有多大。当你在沙滩上闲坐着的时候,你很容易感觉还不错,但第二天醒来去上班的时候,却被一系列不愉快的症状所淹没。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夸大客观测试脑震荡的重要性。
在我与神经科医生的后续预约中,我得到的唯一客观的测试是血压测试。那是天一样高,但我告诉了他们我认为他们想听的话:“我感觉好多了。我的焦虑好多了。这只是一次,因为我很紧张。”
我只是想离开墨尔本,把所有的创伤都抛在脑后。
所以,当被要求给我的头痛打个分(满分6分)时,我回答说:“零分。”我允许自己相信这些谎言,因为我非常想恢复健康。
我还透露了我对抗抑郁药的反应,对方的回答是扬起眉毛:“嗯,奇怪。”
我不应该低估我的症状的严重性,但我不是第一个告诉医生他们想听的话的人。事实上,低估脑震荡的症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AFL球员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23年接受潜在脑震荡的男性球员中,有十分之一没有报告他们的症状。
量化身体和情感感受是非常困难的,当工作岌岌可危时,人们更有可能淡化或彻底撒谎。
虽然我很高兴神经科医生同意了我的诊断,从而免去了预约,但我想一定有更好的工具和技术来检测脑震荡。
果不其然,有无数个。
在美国,脑震荡及其相关的健康风险几十年来一直是国民的良心,因此有数百家专门的治疗机构。大多数中心都有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涵盖了广泛的治疗(语言、认知、职业和身体)和专门的诊断和治疗设备,如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和计算机视觉和平衡跟踪技术。
我来到悉尼开始我的学业。在新生入学日,当课程管理人员向我解释悉尼大学法学院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法学院之一时,我不禁感到自豪。
这足以让我避免每次看电脑时前额的剧痛。我想这一定是后天习得的反应。然而,当我那天下午回到家时,我太累了,所以在日落之前就上床睡觉了。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开始学习时,我被可怕的感觉淹没了。我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悉尼的气温是华氏30度,但那天晚上我太累了,我穿着袜子、运动裤和套头衫睡了——至少我试着睡了。那天晚上我不停地抽搐,神志不清地沉思。接下来的几天我都累得不敢出门。当我打电话给在墨尔本的妈妈,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身体上做不到。我怎么了?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承认。
我推迟了在这门课上的名次。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心烦意乱,又一次虚弱起来。后来有人向我解释了这一生理过程,但当时我无法理解头部受伤怎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全身反应。
尽管我心存疑虑,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质疑医生的裁决。我把这些症状归因于焦虑,当我的朋友问起时,我只是告诉他们“法律不适合我”。
虽然我被头痛、脑雾、头晕和不断的紧张所困扰,但我试着把这种环境的变化当作康复来对待。我很沮丧,因为我不能上大学了,但至少我很高兴能远离墨尔本泡沫的可怕担忧。
我的脑震荡让我感到虚弱和孤独——我一谈起这件事就充满了悲伤。
虽然有几天,只要一走进阳光,我的心就会疯狂起来,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的症状又好转了。这种起起伏伏的恶性循环是一种令人泄气的经历。我偶尔会有一两个星期感觉还好,但在试图重新投入正常生活后,我又崩溃了。
那是2023年3月,离我大学毕业仅六周,所以当我接受了北悉尼一栋高层建筑的一份工作后,又一次出现了症状时,我不应该感到惊讶。
当我从电梯走到办公室楼层时,我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我感到浑身发抖,就好像我走着走着脚下的地都要塌下来似的。办公室的荧光灯太亮了,我不得不把眼睛盯在地板上。光是看着电脑屏幕,我的脑子就嗡嗡作响。我试着坚持下去,但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是如此痛苦和疲惫,以至于我直接上床睡觉了。
我几乎没有睡觉,但我试图在早上洗个热水澡来恢复活力,我的身体经常痉挛和抽搐。我坚持了四天后才尴尬地决定放弃。
我的精神和身体降到了最低点。这是第一次,不只是我一个人被牵连到无法正常工作——我也让雇主和同事失望了。
我女朋友恳求我就我的脑震荡再征求一下意见。在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的推荐下,我被转介到墨尔本一家专门从事神经系统康复的诊所。
我听过几个被神经科医生错误诊断的人的故事,他们继续在这家诊所接受治疗,重新发现了他们的生活。我谨慎乐观地认为,它或许能找到答案。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有一小部分希望这将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一切都没有错。
我在受伤大约一年后参加了第一次咨询。我的症状达到了顶峰
与之前的诊所相比,这家诊所在护理、理解、测试和技术方面的差异确实令人困惑。他们不能单腿站立,闭上眼睛30秒,也不能用划桨杆来跟踪眼球运动。不到60分钟的评估后,我并没有被打发走。不,我在三个小时的严格考试中经受了考验,并在考试中发现很多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
诊所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如红外线护目镜、眼动追踪测试、平衡追踪系统、心率监测器和感觉运动协调测试,以提供客观的诊断,对我来说,它概述了四个方面的不足,清楚地解释了我的症状。
对光线的敏感和对屏幕的厌恶是由于我的眼睛无法准确地注视、保持稳定的凝视和正确地跟踪目标,同样也导致了持续的头痛。在这些测试中,我的成绩在同龄男性中垫底22%。由于前庭系统的缺陷,我感到头晕和迷失方向,在测试中,我的前庭系统排在倒数19个百分位。
疲劳、脑雾、紧张和头晕可以用我的自主神经系统失调来解释:当我从躺着过渡到站立时,我的心率每分钟上升了59次,这是诊断为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的依据。
最后,我的医生诊断出小脑功能障碍,导致认知障碍、平衡和运动技能缺陷。
除了脑震荡后症状量表,我还获得了脑震荡临床概况筛查工具、患者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障碍评估、中枢致敏性量表和头痛残疾指数。
这些问卷不仅帮助我理解和传达了我的症状,还让我的医生全面了解了这些症状是如何影响我的生活的。不管我用什么方法量化我的症状,我都不可能对客观测试的结果提出异议。我的视力、前庭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和小脑的缺陷导致我无法完成日常工作和运动等日常任务。
毫无疑问,这其中也有创伤压力的因素。脑震荡的专业术语是一种轻微的创伤性脑损伤,因此这种经历的创伤性质是固有的。不管我是否知道,我的大脑一直处于一种威胁的状态,这导致了巨大的、使人衰弱的焦虑。我的医生强调了心理治疗作为康复过程一部分的重要性。
这个测试项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减轻了病人表达非常主观和独特感觉的负担。有时我只是感觉不太对劲,挣扎着找语言来形容这种痛苦。有了像“正义”和“平衡追踪系统”这样的测试,病人可能会抱怨“我感觉不像自己了”或“我头疼”。一个合格的、最新的医生将能够根据测试量身定制一个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老实说,感觉就像我走进了时光机,20年后才发现这家诊所,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是标准。我得到了一个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可以在家工作。
我开始每周与一位心理学家会面,他对头部创伤的影响非常了解。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经历。我的心理医生向我解释了头部创伤患者花费数年时间寻找合适的医疗援助是多么常见。同样,他解释了悲伤和失落的情绪在脑损伤幸存者中是多么普遍。脑震荡可以摧毁你的基础,剥夺你让生活有价值的乐趣——毫无疑问,我就是这样。
最后,我觉得自己被理解了,好像我并不孤单,那不是我的幻觉。
定期的心理治疗和每月与脑震荡诊所的远程医疗预约相结合,帮助我在短短三个月内实现了减少焦虑和抑郁的最终目标。我的认知功能、能量水平和情绪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精神上我又找回了自我。我每周回去工作几天,虽然我的症状没有消失,但我很高兴又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我的焦虑看作是脑震荡的直接结果,而身体上的症状则是焦虑的结果。我的医生毫不含糊地解释说,事实并非如此,有明显的生理缺陷导致头痛、光敏感和头晕。
我过早地回到了我深深怀念的活动中。我开始冲浪,跑步,去健身房,再次参加社交活动。虽然我的症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仍然存在。
我在一家零售店工作,天花板上的灯光刺痛了我的眼睛,从我的后脑勺到脖子都放射出一阵剧痛。这令人难以置信地不舒服,但我在精神上很放松,这足以阻止我免受身体上的胁迫。
意识到自己操之过急,我减轻了负担。我恢复了我的康复计划,每天在固定自行车上锻炼20分钟,同时进行视觉和前庭锻炼。我看到了稳定的改善,并享受了几个月的相对幸福。我的症状仍然存在,但毫无疑问减轻了。
尽管如此,颈部疼痛和对光敏感仍然存在,随着我重新发现精神健康的新鲜感开始消退,我越来越被他们的固执所困扰。我很想留在悉尼,所以我继续定期通过远程医疗与我在墨尔本的医生联系。他向我解释说,颈部疼痛是脑震荡受害者的常见症状,反过来说,手工治疗是康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议我做些轻微的按摩来缓解紧张。
我答应了,尝试了放松按摩、整骨疗法、针灸和感觉剥夺坦克——所有这些不仅无效,而且加重了我的症状。
沮丧之下,我研究了更好的替代方案,发现了一家理疗师经营的诊所,“为脑震荡患者提供基于最新研究的专家治疗”。我预约了一次,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手工治疗,以补充我从墨尔本接受的项目。
在最初的咨询中,医生正确地主动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测试。我又一次跟着一根冰淇淋棒上下左右,单腿站立。他们同样对我的脖子进行了检查,从各种检查中得出结论,这是我身体不适的原因。究竟是压力还是鞭打的结果,目前还不清楚,但它“非常紧”,让我头痛,给我的视觉系统带来压力。
为了表示反对,我向医生出示了我在墨尔本收到的视力和平衡测试的结果,他们辩称:“也许你以前就有过。”
我又一次感到矛盾,非常怀疑,但又抱着一丝希望,也许会有一条不需要艰苦的康复之路。“为什么不呢?”我想。
我接受了一些颈部按摩,经过一两个疗程后,我的脖子有了轻微的改善。然而,随着按摩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我的症状变得难以忍受。
我取消了约会,再次陷入痛苦之中。我头疼得厉害,脖子疼得厉害,只要有一点点蓝光,我的眼睛就发抖。
我刚刚回到工作和运动中,现在我几乎不能完成轮班或散步而不感到疼痛。我充满了愤怒:身体上我觉得我又回到了起点。
虽然我的焦虑还在,但我很难表达我在这一点上感到的沮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欲望离开沙发过自己的生活。但现在我只想去跑步或和朋友喝一杯。
在精神上,我又恢复了我自己,我想象着当我达到那个目标时,我所有的痛苦都会消散。然而,我的身体完全受损了,经历了这么多挫折,我甚至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随着2023年接近尾声,我开始觉得在悉尼是浪费时间。我不再这样看待它,因为它给我带来的精神解放是极其重要的,但回到家专注于我的康复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
今年年初,我回到了墨尔本,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可量化和客观的健康指标的巨大改善。
当我集中注意力时,我的眼睛不再颤抖了,我的平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的心率也与正常水平保持了一致——尽管还没有达到正常水平。我不得不时不时地离开电脑休息一下,因为对光敏感和头痛仍然存在,但我的注意力水平很好,所以,调整一下我的情绪和精力。
最重要的是,随着客观测试工具的改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又回来了。神经康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捷径可走。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尽管脑震荡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每一个遭受长期症状折磨的受害者都绝不能失去恢复正常的希望。
不过,我不应该处于这种境地。如果得到有效的早期治疗,我本可以更早地回到工作、运动和健康快乐的生活中。脑震荡很可能只是我人生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
无可否认,澳大利亚的对话正在发生变化,但仍有太多的人继续受苦。
每个遭受脑震荡后综合症虚弱影响的人都必须有简单的途径获得有效的医疗治疗,而目前在这个国家,这并不是现实。
这篇文章不能代替专业知识所有健康建议,不打算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也不能替代您自己的健康专业人士的建议。如果你有任何具体的问题a关于任何你应该去的医疗问题咨询你的医生。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需要支持,请联系生命线131114或Beyond Blue。如遇紧急情况,请拨三零(000)。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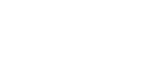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