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遛狗,但凯伦有别的主意我是这样赢的
一个60岁的女人,头发很贵,穿着荧光紧身衣,从蕨类植物中跳了出来,伸出双臂挡住了我前面的路。“停,”她说。“到此为止。”
我做到了。我得把她推开才能通过;她挥舞着双臂,像守门员一样屈膝,准备向左或向右跳跃,阻止我的进步。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是在点球大战中,还是被一个好色的隐士选为舞男。当我休闲的时候,很少有人在身体上阻止我的进步,所以当我在森林里被穿着弹力织物、手臂细长的女人伏击时,我通常会吓呆。今天我也是。“你他妈在干什么?”我温柔地问。

“卡伦”现象最近被广泛报道。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一大堆中年白人妇女在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体重,发脾气,对商店工作人员发号施令,告诉陌生人哪里可以停车,哪里不可以停车,向骑自行车和踏板车的人挥舞手机,并威胁要逮捕他们。我在YouTube上看到过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巡逻,但我没想到会在离CBD这么远的地方被卡伦教。
“你不能带着你的狗沿着这条小路走,”她说。“这是一个国家公园。这里不能有狗。转身。”
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对这位自封的(是的,被封的——她大声喊着橙色的特朗普黏液,也许是模仿另一位长城建设者)治安官的回答是,自称是领主或不法之徒——凌驾于或超越于她的规章制度之上。
以前,我会告诉她,我根本不在乎公园护林员和裹着收缩膜的义务警员是怎么想的。有一段时间,我会告诉她,如果她对混乱的理解是狗在不该去的地方游荡,那么我对混乱的理解更大,也更矛盾,在这个世界里,控制狂从树后跳出来,训斥那些带着狗散步的无辜的人,他们在午餐时喝了七罐啤酒。以前,我会告诉她别挡我们的路,因为薇玛和我已经渡过难关了。
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与冷酷的独裁者的斗争总是以我的失败告终;罚款、警告、恐吓、警告,我的违规行为被记录下来,并在某个机构的电脑上积累,直到他们达到了需要敲我门的级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你不能用诚实的异议、逻辑或勇敢的不服从来击败那些维护法律秩序的怪胎。这样的人太多了,规则就是规则,在规则的范围之外是一片黑暗的混乱,健全的人停在为那些膝盖承受着比他们应该承受的大两倍的自我负担的人保留的空间里。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才学会这一点——但我现在知道如何超越社会对我做正确事情的期望。我想出了一个方法。我称之为肖顿策略。当她挥舞着双臂,哭诉罚款和护林员,威胁要叫警犬队来的时候,我指着威尔玛说:“她是一只治疗犬。”然后我指着太阳穴说:“NDIS”。那个想要成为治安维持会成员的人垂下双臂,开始茫然地环顾四周,仿佛天空变成了紫色,鸟儿变成了鱼。
我不是《肖特的游戏》的新手,当然也不会笨到提名一种特殊的残疾。为什么要命名一种综合症或恐惧症,限制我痛苦的范围和我挣扎的深度?不。我只是指着我的头,问题区域,其中的问题可以是任何东西,因此是一切。我精神分裂、偏执、躁郁症、抑郁、焦虑……和计数。妈的,就这女人所知,我投了绿党的票。
如果我是如此痛苦,那么我的治疗犬一定是一个嗅着裆部的救星,用无条件的爱来缓解我的疾病。
当她的眼睛清醒了,鸟儿的鳞片也掉了,这个女人可怜巴巴地连连道歉。她感到羞愧和抱歉,说如果我想在散步时吃点零食,她车里有一个三明治。尽管她有其他缺点,(上面列出的)她是一个很好的零食制造者。熏鳟鱼和黑麦莳萝。
不是说这个女人应该知道真相,但薇玛的事我没有撒谎。所有的狗都是治疗犬。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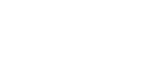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