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恐同的世界里长大——然后我生命中的每个人都开始出柜


上帝讨厌同性恋。
在我16岁生日的那个夏天,我们第一次搬到堪萨斯州的托皮卡,迎接我们的就是这个牌子。
“士兵死于同性恋婚姻”,另一条红、白、蓝相间的条纹写道。
几十个人站在路边,把纸板吊在头顶上。我被他们的热情弄糊涂了,从我们的绿色福特金牛座的窗口往外看。
“那是什么?”妈妈在等红灯时刹车,我问道。
“威斯特布路浸信会,”她皱起眉头。“我在新闻里见过他们。他们当面看更恶心。”
为了避免目光接触,我扫视了一下纠察队员。比我11岁的弟弟还小的孩子在头顶举着牌子。
“有时候我们不是浸信会教徒吗?”我问。根据军队派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是浸信会、长老会、联盟、路德会或无教派。在两个国家,四个州,九个家庭之间,我们加入了最遵循圣经的当地教会。
当交通灯变绿时,妈妈踩下了油门。“我们不是那种浸礼会教徒。”
我哥哥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看见了一个标志。“什么是烟?”他问。
妈妈和我对着后视镜交换了目光。
“对于喜欢男人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刻薄的名字,”她说。“圣经说这是错的,但这些人太过分了。”
爱罪人,而不是罪,是我们被宽恕的另一种选择——这是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想法,但其微妙之处同样危险。
爸爸妈妈定义了我的现实。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过要质疑或逃避它。从我记事起,电视和玩具就被仔细审查,以符合我们福音派基督教的世界观。妈妈说彩虹布丽特的魔法很邪恶。芭比娃娃会让我饮食失调的。不知什么原因,生活在蘑菇里的神奇的蓝色生物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榜单。当爸爸说我的卷心菜娃娃在我打盹的时候走到厨房去吃汉堡时,我相信了他。我很容易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如果要我精确地指出我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我家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我会说那是在我们与威斯特布路浸信会发生冲突之后不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入公立学校,我十几岁时的大脑,随着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无法摆脱一种挥之不去的好奇心: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会怎么样?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佛教徒而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吗?如果我是在威斯特布路浸信会这样的教堂长大的,我还会在托皮卡的盖奇公园高举充满仇恨的标语吗?
从那时起,我的宗教信仰在一连串的质疑中逐渐被侵蚀。我没有变成一个异教徒,沉迷于酒精、毒品和性。作为一个社交笨拙、害羞的十几岁女孩,我以更微妙的方式反抗。我抵制传统的约会,阅读关于其他宗教的书籍,并与我的异地男友一起突破了我的真爱等待禁欲承诺的界限。我离基督教越远,我就越怀疑这个世界和我在其中的位置比别人告诉我的要大。
在我精神解放的同时,我的家人也经历了他们自己的转变。我父母离婚了。我弟弟透露他是同性恋。一年后,我妈妈告诉我,她和一个女人有了终身伴侣。将近十年后,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福音派基督徒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同性恋恐惧症时,我注意到一种我当时认为令人不安的趋势。
无论是外表、举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一生中吸引的许多浪漫伴侣都比一般的直男、顺性别男性更有女性特征。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误认为是同性恋。还是我错把他们当成直男了?即使事后看来,我也没有答案。他们的故事不是我能讲的。
他们的限制也不是我的。我并没有忘记“三人原则”:我的兄弟,我的母亲,我自己的伙伴。我怎么会错过了与我最亲近的人如此明显、重要的部分呢?为什么我不能弄清楚在我床上的人的性别身份?作为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我经历了结婚、痛苦的离婚和无数次约会中的不幸,然后把镜子对准了自己,反思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自己的性别身份。

离婚两年后,我做了一件我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做的事:我回到了教堂。我发现,一神普救派教会的精神社区似乎特别适合前福音派基督徒。他们不在乎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致力于对真理和意义的共同探索,他们接受所有人。就连妈妈和她的伴侣也跟着我走到临时搭建的可堆叠椅子上。
独立日那一周,舞台上到处都是美国人的随身用品。你是一面伟大的老旗帜。你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唱诗班突然唱起了一首烂醉的小调。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隔壁的那个男孩,”我低声对妈妈说。
她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五年级的时候,隔壁的男孩在合唱队的时候大声唱了同一首歌。当时,有传言说他喜欢上了我。
妈妈强忍着笑。“他太gay了。”
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从这句话中得到了一种不敬的快感,就像我小时候告诉爸爸我加入了一个有佛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教会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一样。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她的话记在心里。他有那么gay吗?我没注意到。
妈妈从小让我相信,一个人的表面特征,比如声音、对运动或乐器的喜好,与他们的性取向无关。作为一个中间类型的女孩,我很好,约会的对象是男性-女性光谱的中心。但在我的婚姻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和力量结束两年后,这句副歌就像在教堂中央迎面相撞一样击中了我。
歌曲快结束时,我的脑子转了起来。女同性恋?那样就容易多了。全世界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妈妈也会为你感到骄傲。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产生过性吸引力,但我几乎总是有一个女性闺蜜。我是同性恋吗,还不知道?
当你看到生活中的一种模式时,最终你会意识到它的共同点就是你自己。直到遇到她最好的朋友,妈妈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对女人有吸引力。我的一些前任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似乎还在寻找自我。也许我身上还有更多的东西想要被发现。
那个星期天之后不久,我决定暂时不去关注约会中对我来说如此自然的情感和友谊部分,并发誓要关注是什么让我兴奋起来。我从看女同性恋色情片开始。事后看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看色情片是糟糕的第一步。除了一段关系之外,我过去也没有和除顺性男性之外的任何性别交往的经历,这不是我理清头绪的方法。
在一神论派的烧烤会上,一位素食女性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问我:“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注意了。她是那种跳出皮肤,直接进入我灵魂的人。我们的友谊开花结果。我试着想象。如果她没有结婚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异性恋。还是什么都没有。我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在我允许的时间内得到答案,因为我太害怕了。
敞开心扉审视自己的性取向,就像16岁时害怕上帝会召唤我去非洲偏远地区传教一样。我听过布道。有人死在那里。我真的会为耶稣做任何事吗?对真理?难道我从婚姻中醒来,从伴侣关系的所有规范中醒来还不够吗?接受他人非传统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一回事。让它们进入我的内心,如果它们真的存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以不同于异性恋、顺性别女性的身份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不适?
当我面临走向真理或远离真理的选择时,我不可避免地选择走向。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确定前进的方向,但最终我找到了前进的勇气:从宗教到灵性,从亲生家庭到选择的部落,从社会对爱的定义到塑造我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心痛和困惑。
为了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爱,我必须无情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先入之见。我默认接受了什么样的性别角色?我愿意变得多么脆弱?我愿意在未知的世界里走多远?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不再从男人那里寻求认可和归属感,而是向我选择的家庭敞开心扉:我的母亲和她的伴侣,她伴侣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我的兄弟和他的男朋友。在这个部落里,我们更多的是由爱而不是血缘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为做自己而奋斗的过程中互相鼓励,我让自己完全自在。

今天,我和一个从我开始质疑自己性取向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陪伴着我的人在一起。我还在学习如何大声地做自己。双性恋、泛性恋、半性恋、灰色王牌——所有这些标签都指向了我的一部分。就像没有任何宗教能够清晰地表达我灵性的广度一样,也没有任何标签能够定义我的全部性取向。
我不再执着于寻找答案,而是学着拥抱问题。我不是一夜之间就退出异性恋的。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其中包括阅读酷儿作家的回忆录,在和我现在的伴侣(他认为自己是直男、顺男)计划婚礼时,以质疑的方式出柜。
称自己为异性恋、顺性女性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听起来很异端。我43岁,再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酷儿这个词,在我看来,这个词根本没有定义。随着进展,或缺乏进展,在我们国家的法庭上上演,我准备让大家知道,我不仅仅是一个盟友。我看到这些牢笼,我想离开——从我们对他们的心态中走出来,这种心态正在破坏我们的政治格局,破坏我们最脆弱的孩子,破坏我们爱自己的能力。是时候说同性恋了,在我们的个人旅程中,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如此的伟大。
梅丽莎·戈普-华纳是一个有创意的no关注人际关系的小说作家人际关系及其与性取向和性别的关系。她的文章和人物曾在《出版人周刊》、《榕树评论》、《作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她通过bimo推广了这一类型第二次书评,不同的作者和生活经历。更多信息请访问melissagopp.com。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找出我们在这里需要什么,然后给我们发一份建议书。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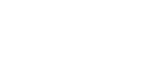
发表评论